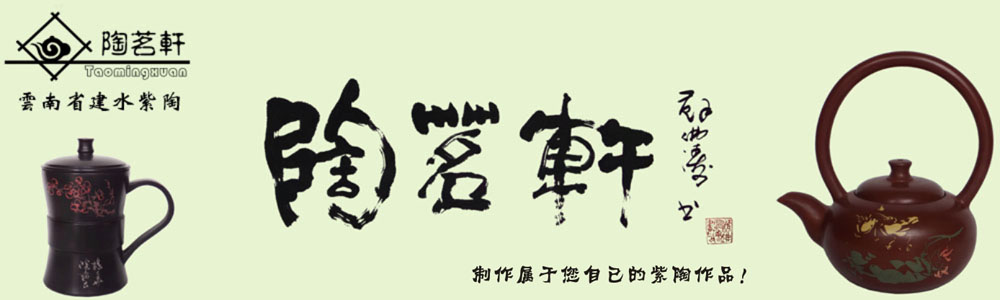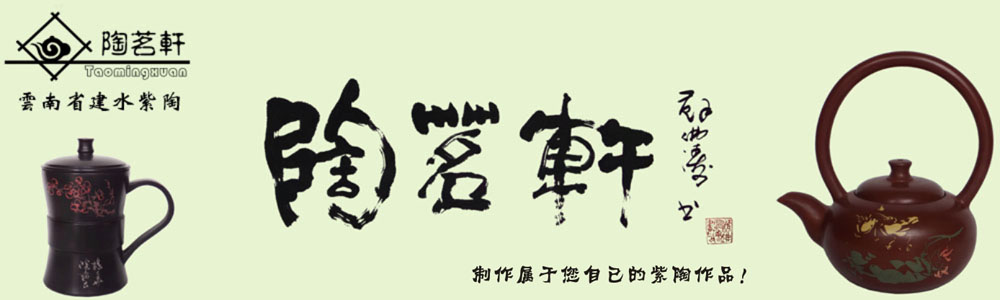|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吴白雨

“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在当代科学技术与机器文明的逼迫下,艺术之道已身陷不断建构又被解构的境地。不能说科技对当代艺术的变革毫无可取之处,但是艺术之真,自然之美在当下失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艺术观念的如何更新,艺术形式的穷尽所奇,艺术的本质仍然不会超出人类精神及心灵深处的自我反省与生命关怀。面对我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迅猛退化,盲从西方的激进者有之,不思进取的复古者有之,奴隶于商业炒作的投机者有之,承认退化而又无力回天的恼羞成怒者有之。当然也有不断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怀着对文化尊严丧失的悲恸,一边以对艺术理想的执着探寻心灵无法到达之处的深刻内省,一边以卧薪尝胆的身体力行砥砺当代艺术之堕落。他们放弃无谓的口舌纠缠,回归到艺术生发的原点,力图以一己之光点亮艺术复兴的苍穹。
古城建水,虽地处边疆,但在这里,风俗得以保存,人情更为纯朴,对传统更加敬重,最重要的是这里有陶。要知道,在所有艺术门类之中,若要论及人与自然之融通,朴素与高贵之对唔,艺术与工艺之相契,没有什么比陶艺更为传统和适合的了,它是根植泥土的劳作,也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文明和最重要的造型艺术之一。
在四千余年的建水陶历史中,历代劳作者们以朴素之心发现了建水陶的朴素之美。他们在与泥料长期的交往中深谙它的个性,并从几十道繁杂的工序中,智慧地创造出建水陶“阴刻阳填、无釉磨光”的独特工艺。刘也涵与建水陶的第一次偶然相遇,便激起了他的艺术理想和创作热情。2007年,他把家从北京搬到建水陶的起源地——碗窑村。他视泥土为己,以劳作为乐,与村民为友,以至于这个地道的满族汉子也能端酒碗,吃辣椒,操几句建水土话,不知者常常误以为此人是邻村的庄稼户。刘也涵不断地深入到建水陶的工艺研究和艺术创作之中,他固执的要陶工拉出难度极高、体型硕大的泥坯,他不容许自己的作品有任何瑕疵,他摩挲着这些瓶瓶罐罐彻夜不眠,他在建水陶上绘制温情的钟馗、羞涩的仕女,他是建水陶艺界的特立独行者。
特立独行者往往是真正的思想者。刘也涵知道,建水陶是可以将诗文、书法、绘画、篆刻等相互融合的一门独立艺术,它比纸张更加坚固耐久,既可满足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又能触摸把玩,极富文人意趣。正如陆子刚的玉器、时大彬的紫砂、金西崖的竹刻、西泠八家的制印,都源自于传统文人对物性之善的直观和器物之美的怀念。刘也涵沉溺于建水陶的艺术创作之中,这不是笔墨技巧在陶丕上的复制,这是他对文人生活体验的回归,自我心灵休憩的获得。
刘也涵对建水陶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有着其他陶艺家难以具备的条件,一是他拥有三十余年对传统艺术理论和技法研究的经历。他很早就从中国画科班出身,修养全面、技法完备、功力深厚,获得了一系列国家级重要奖项,并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二是他师从画坛名宿——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导师李少文教授,并一直是李绍文教授工作室的核心研究员之一。身处我国最高艺术学府丰厚的人文环境,使得他随时处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有着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过人的创作能力。正因如此,刘也涵的建水陶创作才能够呈现出艺术格调承继传统,形式语言立足当下的开拓性特征,他的作品器形与图式浑然一体,色彩与质地相互映照,泥性与笔性合二为一,观感与触感彼此生发。
任何艺术创作,最终要落实到艺术语言的创造上,艺术语言的缺失将致使作品本身失去意义和价值。文以载道,循道而长。刘也涵闲居建水,甘守寂寞,安于静寂独处的田园生活,深浸于人生之参悟,哲学之思辨,诗词之研习,笔墨之锤炼。他不斤斤计较于传统书画在建水陶上的精致描摹,而是体察“文道”与“物道”之共性,探索水墨与陶土之融通,既保持陶器朴素之品质,又植入文人审美之格调。“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他的作品源于传统,却不趋同传统;发于心境,却不追从时风。刘也涵建水陶艺术的个人风格和艺术语言的建构,在生活蒙养和自我反省中自然生成,意境追溯古典,意识根植当下,正如他所创作的钟馗、高士、少女、牧童,无一不生趣盎然、温情脉脉、羞涩含蓄、天真烂漫,令人心生爱怜,又会心一笑。这些不正是我们心中丧失已久而又渴望得到的纯真、善良、活泼之美吗?刘也涵作品所透射出的艺术的悠远与崇高,离我们既远且近,如此亲切而又新鲜。艺术语言的独创,使得他的作品匠心独具而匠气无存,融艺术之道和工艺之美于一体。
刘也涵作为一位阅历丰实的中年艺术家,对艺术自然有着更加深澈的感悟。他摒弃浮华炫巧的技艺卖弄,专注于艺术内涵的发掘。他的建水陶创作,意向平和深邃,并呈现出他对历史的隐喻和人性的关怀。《火红年代》系列是他长期以来最重视,也最重要的创作题材之一。他试图以陶土之善,艺术之真承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伤痛与感怀。这不是取巧猎奇,也并非无病呻吟,这是刘也涵作为被历史激流冲刷的一个生命个体,在时代变革和生命逆旅中的沉重哀艳。巧妙的是,他对此不是简单的再现或是戏谑性的批判,他以纯真、浪漫、稚气、天真、可爱的少女来表达对曾经伤害的回望。她们忧郁、善良,对现实无法逃避,对未来又充满希望,她们不逃避也不谴责,她们以真,以善,以未泯之童心来刺穿记忆与内心深处的隔膜。不得不承认,在任何艰难的历史时期,哪怕是贫穷、混乱、疯狂、伤痛,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崇高精神的向往都不曾被掩埋。相反,由于这无法蠲除的悲恸的反射,人性之美才显现出如此耀眼的光芒,这光芒穿越时空直射当下,它唤醒了我们对艺术之善的渴望,它让获得了物欲满足却丧失心灵之美的商业艺术无地自容,它使不思进取、毫无意义的传统卫道士们自惭形秽。火红年代的歌谣虽然已随着那个时代游戏的落幕而渐去渐远,但它留下了我们对真诚的渴望和青春的憧憬。刘也涵以建水陶最本质的艺术语言,默默编织着“火红年代”的童话,它消解创伤,营造信念,它既扎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上,又绽放在当代的天空之中,刘也涵建水陶艺术的价值和高明之处正在于此。
他当然是个的特立独行者,刘也涵正以高蹈之志,澄怀之心,踽踽笃行在建水陶艺术创作的历史延续中。
庚寅玄月于蒲风书坊



以上图文选自 刘也涵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uyehan2011 |